中国现代文学“以文见史”的写作传统
所谓“以文见史”,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汗青互动关系的归纳综合,它既是作家面临汗青的观念传统,又是作品处置文本与实际关系的写作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在反思汗青、存眷实际方面成绩卓越,各个时期的文学潮水中都存在一个清楚的汗青维度。是以,文学作品对熟悉中国近当代史具有弗成轻忽的能动作用。言说汗青照样当代作家试图借汗青以加强话语力气的策略,当代文学批驳中也始终有一个潜在的汗青尺度,文学作品与汗青的关系成为文学批驳的准则之一。
施展文学对熟悉汗青的能动作用
以往学界对当代文学传统的梳理主要聚焦于实际主义、浪漫主义、当代主义传统,或写实、批判、抒怀、年夜众化传统等。这种研讨范式有待完美,由于上述对文学传统的归纳综合只包括了创作办法、文本特性、教养主旨的传统,而没有包含社会学意义上的“写作传统”和“文类功效传统”。中外文学史上,文学介入汗青言说是常有的征象。文学在中国近当代史上施展了紧张作用,中国当代文学与汗青深度领悟,因而积淀成一种前后接踵、堪称传统的写作征象,并演化为具有本色意义的写作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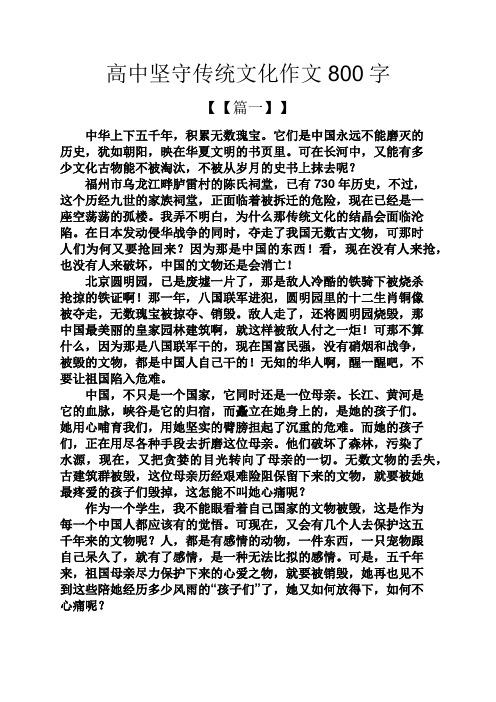
当代文学对汗青的认知作用是弗成否定的,文学研讨理应看重这种作用。在汗青学研讨中,鲁迅、茅盾、老舍、丁玲、闻一多等人的古迹和作品常常被看成佐证史料而引用。当代文学可以或许被用作汗青研讨之辅助的基本缘故原由正在于它固有的“以文见史”传统的存在。站在文学的态度上,完全有需要以文学为本体来考察这一传统的诸多方面,这对把握作为特殊汗青的百年中国文学史是必弗成少的。
“以文见史”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传统。梳理这一传统有助于懂得新文学看重汗青表意功效的特性,从而更好地舆解当代文学自动承担汗青责任的机制。文学介入汗青建构的传统在五四文学之前的提高人士那边就已经开启。中国当代文学是一种善于到汗青中追求资本的文学,当代作家在“人”的建构进程中,首选的是汗青批判的路径,而不是将世俗生涯正当化的路径,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人都选择了前者。
汗青是中国当代作家倾心审视与观照的一片邈远、深邃深挚的疆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都写过孔子的古迹,如郭沫若的《孔役夫用饭》、曹聚仁的《孔老汉子》、冯至的《仲尼之将丧》、陈子展的《楚狂与孔子》等。中国古代汗青上的风云人物赓续呈现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包含人文始祖女娲(鲁迅《补天》),汗青英雄伍子胥(冯至《伍子胥》)、项羽(郭沫若《楚霸王自尽》),精力气节的代表人物文天祥(郑振铎《桂公塘》),及浩繁能臣谋士,如信陵君(廖沫沙《信陵君之归》)、苏秦(魏金枝《苏秦之死》)等。此外,歌唱崇高文人的作品中亦不乏佳作,如郭沫若的《司马迁发愤》、何其芳的《王子猷》、唐弢的《晨风杨柳》等。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汗青书写,是沟经由过程去与当下的精力通道,有助于匆匆进读者对汗青的认知和懂得。
多维因故旧互作用更新写作范式
中国汗青精力是当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最牢固的基础。“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人文化成”“以文传人”“经国之年夜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惟,都与“以文见史”传统有亲密关系。而对“国度”“提高”“将来”的分歧懂得,终极决议着这一传统在文学成长长河中分歧的承继与拓展方式。
“文史不分居”的观念影响到当代作家的写作方式,作为一种文史合一的写作传统,它有深远的汗青配景和深入的实际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前驱者首开“以文见史”的先河。在新文学活动鼓起之前,汗青演义已蔚为年夜观,这是匆匆动新文学产生的一个不该被疏忽的配景。文史兼修的教育方式和文史兼备的常识布局,对五四新文学家处置文学与汗青的关系有直接影响,对此后作家也有深远影响,古典文史观是匆匆进这一传统形成必弗成少的文化配景。
当代汗青观的变迁对“以文见史”传统的形成具有决议性作用。从传统到当代,当代作家逐渐熔炼出极新的汗青观念,如进化论汗青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新汗青观切实其实立对文学创作影响伟大,它转变了文学形象、文学存眷点的总体魄局,文学离别了专写上层社会的期间,而进入侧重书写社会中基层的期间。在走向年夜众与背向年夜众的选择中,汗青观所起的作用弗成轻忽。
中国革命与当代文学的亲密关系,使文学自然地存眷汗青过程。当代文学的纪实功效十分壮大,平易近族国度重年夜变乱与其文学出现之间的光阴差异常小,这是当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夺目标记。各时期的主流文学周全折射出汗青的风云幻化,文学由此逐渐确立了新汗青观、新写作范式并介入了汗青的意义重构。
“以文见史”传统与中国当代伦理变迁互相关注。新伦理的建构依托汗青资本的例子年夜量存在。伦理回嘴在20世纪30年月前后的汗青小说中年夜量呈现,抗战文学把平易近族平安至上晋升为最高伦理原则。中国作家善于到汗青中追求伦理变更的依托。在这里,伦理变更与“以文见史”传统相遇并形成互相映照的千丝万缕的牵系。
“以文见史”传统与当代审好意识慎密相连。审好意识不是凝固的观点而是汗青性观点。当代化的波折历程铸就了近当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见意义,其特性之一便是审好意识与汗青意知趣互交汇。对史诗风致的寻求、对反映生涯深度与广度的寻求、对年夜众化意见意义的寻求、对社会公道公理的吁求等,都与当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形成互相借力、互相匆匆进的关系。汗青意识对作家审美抱负的熔炼同样至关紧张,“以文见史”有时也会成为匆匆进文学流传和接受的积极因素。
“以文见史”传统与当代文学的情势变更密弗成分。汗青小说、新歌剧、随感录、申报文学、列传文学、叙事诗中都有汗青的踪迹。当代作家突破了传统平话和汗青演义的局限,从而为汗青表达发明了新情势。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郭沫若的汗青剧、朱东润的汗青人物列传、谭正璧的汗青小说等,都在文学情势上发明了新范式,而新范式的诞生与汗青语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关系。
看重文学史研讨的汗青维度
文学史是特殊的汗青,它固然不克不及完全走向“以史量文”,但也毫不能彻底摈弃汗青维度。中国当代文学自身成长的现实状态对文学史撰写提出了汗青尺度方面的要求。对“以文见史”传统的认知有助于评价文学作品的代价。文学与汗青都以存眷人道为条件,这就使某些文学作品在天生审美代价的同时也具备认知代价。从文学的汗青叙事中培育出的审好意识是社会化审好意识,对这种意识的研讨有助于揭示审美代价的动态性和社会性,从而体现出中国当代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的一个紧张侧面。
“以文见史”传统为文学接受者与批驳者带来了指向将来的愿景。文学中的汗青书写老是带着对公道、公理甚至乌托邦的憧憬,中国当代文学的汗青精力并不是“向后看”的精力,而是从“曩昔”透过“如今”而直达“将来”的精力。这一传统不仅折射出汗青纪律,并且用指向将来的愿景为社会提高带来隐形的助力。
文学史研讨不克不及缺少汗青的维度。这里所说的文学史研讨的汗青维度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二是微观层面。所谓宏观层面,便是指对任何文学征象都必要将其置于产生时的汗青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然后做出科学合理的代价评判;所谓微观层面,便是本文所说的写作传统的层面,它与详细作家的创作行动、创作结果亲密相关。在文学史研讨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如许一种征象,即对汗青意义的寻求是许多作家共有的代价取向。例如,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虽属虚构作品,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入的汗青启示。作者老是在重年夜汗青变乱产生后不久就将其出现为文学作品,他的《蚀》《半夜》《林家铺子》等都堪称为20世纪二三十年月中国汗青“立此存照”的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的本土化实际主义创作实践与“以文见史”写作传统在汗青的长河中交汇激荡,取得了丰富成绩。
汗青学的一项紧张功效便是确保群体的知觉不被中止。T. S. 艾略特说,传统起首包含汗青意识,“这种汗青意识包含一种感觉,即不仅感觉到曩昔的曩昔性,并且也感觉到它的如今性”。坚持文学史写作的汗青维度恰是对如许一种“如今性”的出现与保存。
(本文系国度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以文见史’传统研讨(1917—2019)”(20BZW147)阶段性结果)
(作者单元:山东师范年夜学文学院)
